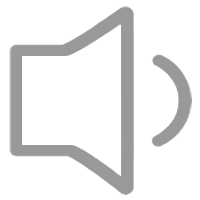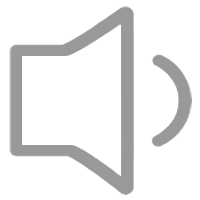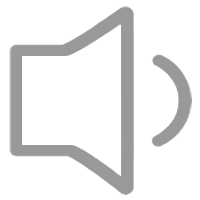送徐無黨南歸序
歐陽修〔宋代〕〔〕
草木鳥獸之為物,眾人之為人,其為生雖異,而為死則同,一歸于腐壞澌盡泯滅而已。而眾人之中,有圣賢者,固亦生且死于其間,而獨異于草木鳥獸眾人者,雖死而不朽,逾遠而彌存也。其所以為圣賢者,修之于身,施之于事,見之于言,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。修于身者,無所不獲;施于事者,有得有不得焉;其見于言者,則又有能有不能也。施于事矣,不見于言可也。自詩書史記所傳,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?修于身矣,而不施于事,不見于言,亦可也。孔子弟子,有能政事者矣,有能言語者矣。若顏回者,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,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。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,以為不敢望而及。而后世更百千歲,亦未有能及之者。其不朽而存者,固不待施于事,況于言乎?
予讀班固藝文志,唐四庫書目,見其所列,自三代秦漢以來,著書之士,多者至百余篇,少者猶三、四十篇,其人不可勝數(shù);而散亡磨滅,百不一、二存焉。予竊悲其人,文章麗矣,言語工矣,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,鳥獸好音之過耳也。方其用心與力之勞,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? 而忽然以死者,雖有遲有速,而卒與三者同歸于泯滅,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。今之學者,莫不慕古圣賢之不朽,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,皆可悲也!
東陽徐生,少從予學,為文章,稍稍見稱于人。既去,而與群士試于禮部,得高第,由是知名。其文辭日進,如水涌而山出。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,故于其歸,告以是言。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,亦因以自警焉。
譯文及注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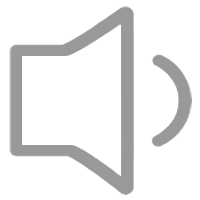
譯文 各種草木鳥獸被歸類為“物”,而世間眾人被歸類為“人”,他們生存在世時雖有分別,然而到了死亡時卻很相同,全部也都變成腐朽、消亡殆盡的地步。而圣賢身處世人之中,他們也需要面對這種生死變化,然而卻和各種事物及世人有分別——他們能在精神、功業(yè)上永垂千古,時間再久也能夠留存。圣賢能夠長存不朽的緣故,就在于他們建立德行、功業(yè)或著作了。一個人能努力修煉個人操守的話,一定能有所成就;若要建立個人功業(yè),卻是受社會情況限制;若要行文傳世的話,則被個人天賦所約束。有些人能建立功業(yè),卻未必有著作留下。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史記》等著作所記,當中有多少人是善于著作的呢?至于有高尚德行的人,更未必
展開閱讀全文 ∨
賞析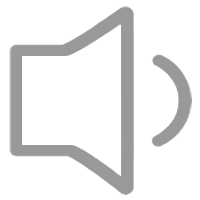
《左傳·襄公二十四年》記載了穆叔與范宣子論何者為“不朽”的一段名言。范宣子以世祿為不朽,穆叔卻認為世祿不能稱為不朽。他說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。雖久不廢,此之謂不朽。”歐陽修這篇文章里所說的“修之于身”、“施之于事”、“見之于言”,就是指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全文用了一半篇幅,論三者之所以為不朽。并將“修之于身”(立德)放在最高地位,“見之于言”(立言)排在第三,這自然不無重道輕文的意思。但這篇文章的主旨,又不在權(quán)衡文道之孰重孰輕,而另有其深意在。
文章重點在第三段——論立言之不可恃。細讀這段文字,會發(fā)現(xiàn)文章在立論上有一個矛盾。前面說,圣賢是不同于草木
展開閱讀全文 ∨,《左傳·襄公二十四年》記載了穆叔與范宣子論何者為“不朽”的一段名言。范宣子以世祿為不朽,穆叔卻認為世祿不能稱為不朽。他說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。雖久不廢,此之謂不朽。”歐陽修這篇文章里所說的“修之于身”、“施之于事”、“見之于言”,就是指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全文用了一半篇幅,論三者之所以為不朽。并將“修之于身”(立德)放在最高地位,“見之于言”(立言)排在第三,這自然不無重道輕文的意思。但這篇文章的主旨,又不在權(quán)衡文道之孰重孰輕,而另有其深意在。
文章重點在第三段——論立言之不可恃。細讀這段文字,會發(fā)現(xiàn)文章在立論上有一個矛盾。前面說,圣賢是不同于草木、鳥獸、眾人的,這種人“雖死而不朽,愈遠而彌存”。他們之所以被人尊為圣賢,長存不朽,是由于他們曾經(jīng)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這里指明立言為三不朽之一。而第三段又說:“文章麗矣,言語工矣。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,鳥獸好音之過耳也。”這是說,立言之士,與草木鳥獸之必然速朽沒有區(qū)別。下文說得更明顯:著作之士“卒與三者(指草木、鳥獸、眾人)同歸于泯滅”,是前后矛盾。
再三涵泳這段文字,就會悟出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。這含而未申之意,正是該文的主旨之所在。第一,古人留下的著作,大多數(shù)僅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諸書中著錄其書名、篇目,具體的作品則“百不一二存”。這說明,歷史對立言之士的著作進行了無情的淘汰。那“百不一二存”的傳世之作,是大浪淘沙剩下來的金子,是經(jīng)受過時代的嚴格考驗的,其余的早就湮沒不存了。于此可見,文章難工,傳世不易。后之視今,亦如今之視昔。這是作者的慨嘆,既以自勉,也以之勉徐無黨。其次,前兩段把“修之于身”、“施之于事”、“見之于言”三者并列為“不朽”,是闡述古代經(jīng)傳中論道之言,反映的是書本上的人生價值觀念。第三段論立言之不可恃,將與鳥獸眾人同歸于泯滅,是歐陽修讀史自悟之理。所謂言之不可恃。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說法。這是從歷史事實中總結(jié)出來的。反映了實踐中呈現(xiàn)的另一種價值觀念。書本上的價值觀念與實踐中的價值觀念如此不同,遂使古今無數(shù)文士為之荷筆彷徨。作者自己一生的體驗,便是明證。因此,文章結(jié)尾用“亦以自警焉”,暗暗透出個中消息。由此可見,這篇文章還表明了自古以來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,因以之警徐無黨。
這樣就見出該文的第一個特點:題旨深隱。歐陽修在其《論尹師魯墓志》一文中提出:寫作應該力求“文簡而意深”,并說:“春秋之義,痛之益至,則其辭益深。……詩人之志,責之愈切,則其言愈緩。”他這篇《送徐無黨南歸序》,無愧于文簡意深、愛深言切的典范之作。
全文立意,既重在表明文之難工與立言之不足恃,抒發(fā)包括自己在內(nèi)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,寫來便情真語切,感慨深沉,這是該文的另一個特點。自古文士,留下來的篇章已僅“百不一二”,其余都“散亡磨滅”,是事之一可悲。留傳下來的文章,“文字麗矣,語言工矣”,又“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,鳥獸好音之過耳”,是事之二可悲。這些人士活著的時候,“汲汲營營”,辛苦忙碌、嘔心瀝血地進行寫作,才達到文麗語工的境地;而當其“忽焉以死”,仍然免不了“同歸于泯滅”,是事之三可悲。末了寫到“今之學者”,窮其一生精力,孜孜于文字著作,結(jié)果是“皆可悲也”。這段文字,飽含深情,既哀人亦復自哀。那種蒼茫萬古之意,發(fā)而為聲,則抑揚唱嘆,慷慨蒼涼。試誦讀第三段,先用“百不一二存焉”,“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,鳥獸好音之過耳也”,發(fā)出深沉的詠嘆;次用“汲汲營營”一個反問句抒發(fā)感慨;再用“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”一收一頓;最后用“皆可悲也”放聲長吁:語調(diào)吞吐抑揚,聲情契合,不僅足以“摧其(徐無黨)盛氣”,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讀此文者無限悲愴。事之不平,積為憤懣。全篇無一憤語,卻飽含憤意于筆端。
這篇文章在藝術(shù)上還有一個特點:結(jié)構(gòu)非常緊湊,前呼后應,針線綿密,因此讀來氣勢流貫,又回環(huán)往復,現(xiàn)出一種感情上的渦流。人手一句,先提出“草木”、“鳥獸”、“眾人”三者都無法逃避同歸滅亡的自然規(guī)律,然后從“眾人”中引入“圣賢”,說他們獨異于草木、鳥獸、眾人。六字扣緊首句,文境穩(wěn)步推開。接下去論圣賢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、施事、見言,將三者平列。繼以比較法層層篩選,步步推出中心。首則拿“施事”與“見言”比,論見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;再拿“施事”、“見言”與“修身”比,引孔子的弟子宰我、子貢善于言語,冉有、季路長于政事,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長于言語、政事的顏回,突出修身為首要之道,立言居三者之末,漸漸過渡到第三段論立言之不足恃,文意暗暗逗出,又層層推進。到第三段,先說“予竊悲其人,文章麗矣,言語工矣”,束以“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,鳥獸好音之過耳也”,“榮華”緊承“麗”字,“好音”緊承“工”字,接榫緊密。又加上“方其用心與力之勞,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”,使草木、鳥獸、眾人匯齊,與篇首第一句“草木鳥獸之為物,眾人之為人”桴鼓相應。復承以“而卒三者同歸于泯滅”、“今之學者,莫不慕古圣賢之不朽”,再提“泯滅”、“不朽”,首尾回環(huán),遙相顧盼,使這篇短文在暢達中有一種遒練逆折的勁氣。這些地方,都見出作者為文煉氣的功力和縝密的文心。▲,參考資料:完善
1、
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鑒賞辭典編纂中心.古文鑒賞辭典珍藏本 中:上海辭書出版社,2012:1439-1443
創(chuàng)作背景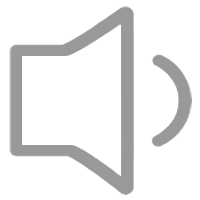
《左傳·襄公二十四年》記載了穆叔與范宣子論何者為“不朽”的一段名言。范宣子以世祿為不朽,穆叔卻認為世祿不能稱為不朽。他說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。雖久不廢,此之謂不朽。”歐陽修這篇文章里所說的“修之于身”、“施之于事”、“見之于言”,就是指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全文用了一半篇幅,論三者之所以為不朽。并將“修之于身”(立德)放在最高地位,“見之于言”(立言)排在第三,這自然不無重道輕文的意思。但這篇文章的主旨,又不在權(quán)衡文道之孰重孰輕,而另有其深意在。
歐陽修
歐陽修(1007─1072)字永叔,號醉翁,晚號六一居士,吉水(今屬江西)人。修幼年喪父,家貧力學。天圣八年(1030)進士及第,為西京(今河南洛陽)留守推官。在西京三年,與錢惟演、梅堯臣、蘇舜欽等詩酒唱和,遂以文章名天下。景祐元年(1034)召試學士院,授宣德郎。三年,以直言為范仲淹辯護,貶夷陵(今湖北宜昌)縣令。慶歷中,以右正言知制誥,參與范仲淹、韓琦、富弼等推行的「新政」。「新政」失敗......[1005篇詩文][100篇名句]
猜你喜歡
梅堯臣〔宋代〕
春云濃淡日微光,雙闕重門聳建章。不上樓來知幾日,滿城無算柳梢黃。......
蘇軾〔宋代〕
紹圣元年十月十二日,與幼子過游白水佛跡院,浴于湯池,熱甚,其源殆可熟物。
循山而東,少北,有懸水百仞,山八九折,折處輒為潭,深者縋石五丈,不得其所止。雪濺雷怒,可喜可畏。水崖有巨人跡數(shù)十,所謂佛跡也。
暮歸倒行,觀山燒火,甚俛仰,度數(shù)谷......
吳文英〔宋代〕
蠻姜豆蔻相思味。算卻在、春風舌底。江清愛與消殘醉。悴憔文園病起。 停嘶騎、歌眉送意。記曉色、東城夢里。紫檀暈淺香波細。腸斷垂楊小市。......
張元干〔宋代〕
夢繞神州路。悵秋風、連營畫角,故宮離黍。底事昆侖傾砥柱,九地黃流亂注。聚萬落千村狐兔。天意從來高難問,況人情老易悲難訴!更南浦,送君去。涼生岸柳催殘暑。耿斜河,疏星淡月,斷云微度。萬里江山知何處?回首對床夜語。雁不到,書成誰與?目盡青天懷今古,......